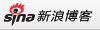- 东北朝鲜族的民间信仰与变迁(一)
- 东北朝鲜族的民间信仰与变迁(一)本文来自中国民俗学网 www.chinesefolklore.org 文章源自:学苑出版社网站[摘要]本文以田野调查的活态资料为依托,对一个世纪以来我国东北朝鲜族的民间信仰及其变迁状况进行了勾勒,并对其成因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我国东北朝鲜族民间信仰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族群所处的独特环境以及人口迁移、经济开发、民族融合等历史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只有拂去社会历史与民族生存史的风尘,才能客观而科学地把握东北朝鲜族民间信仰的特征及其变迁的动因。我国东北朝鲜族的民间信仰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多种信仰传统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在民间具有深广的根基。其中,朝鲜族女性民众由于生存环境与命运遭际等复杂的外部原因以及性别与气质等内部原因,对弥漫于东北乡村社会的种种民间信仰十分痴迷,构成了民间信仰群落的主体。对朝鲜族民间信仰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考察东北朝鲜族族群历史与文化的基础角度,而且对于理解东北区域文化的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一、东北朝鲜族民间信仰生成与传播的背景与我国东北区域的其他民族相比,朝鲜族有着相对复杂坎坷的民族生存史。 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大多数是19世纪中叶以来因逃避灾荒与战乱从朝鲜半岛陆续迁入中国的社会下层民众。从宏观上看,促成这种迁移主要有经济与政治两方面的原因。经济原因是由于朝鲜李氏王朝残酷的剥削和统治,以及朝鲜半岛北部自1869~1890年长达20年的农业歉收和其他灾害,使得广大下层民众已无法生存,被迫跨过鸭绿江、图们江,到地广人稀且统治阶级鞭长莫及的中国边境地带寻找生路,垦殖荒土。政治原因是1876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陆续侵入朝鲜,直到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血腥的屠杀和大肆的抢掠,残酷的高压殖民统治促使朝鲜半岛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纷纷外逃到中国。再加上1931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之后,为了实现“满洲农业、日本工业”的计划,制定了“朝鲜人指导纲要”,强迫大批的朝鲜农民移民中国东北,组织开拓团,垦荒种地。如辽宁省《新宾朝鲜族志》记载:“1939年,第一批集团开拓民,由朝鲜全罗南道移民200户至新宾红庙子一带地区,开拓民都是普通的贫苦农民,他们拖儿带女从朝鲜荣山浦上火车,经7昼夜直达南杂木,然后用卡车送到红庙子。”(新宾朝鲜族志,1994:7-9)在20世纪20年代,新宾县旺清门的朝鲜族只有十几户,到30年代初,已发展到3000余户了。笔者在黑龙江五常地区调查中获知,20世纪30年代中期,该地的民乐乡只有12户朝鲜族人家。1937年,韩国一位名叫孔振焕的人在庆尚北道一次就组织了500户移民到民乐乡,至此,当地才出现了一些朝鲜族村屯。总之,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我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口已增至170多万人。这些因生活所迫而迁移中国的朝鲜国贫民,入境后几乎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生存考验,不仅承受着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的压力,同时,迁移后的安身立命也受到极大的挑战。在调查中获知,许多移民人家都有一部血泪交织的迁移史。如民乐乡红光村一位姓金的朝鲜族妇女讲述,其19岁时(1933年),随父母及姑家、舅家一道由韩国庆尚北道向中国逃荒,一路上母亲晕船,几次险被船主扔进大海;途中因生活所迫,舅舅9岁的女儿被卖掉,她本人也被以一袋小米、一袋荞麦、五袋土豆的代价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受尽磨难。正如辽宁省新宾县地方志所记载的那样,“朝鲜移民迁居中国境内后,由于不服水土,食用发霉的小米,患病死去的很多,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新宾朝鲜族志,1994:9)可是,背井离乡的朝鲜族民众来到中国后,等待着他们的又是什么呢?20世纪初的中国东北,空旷而荒凉,气候恶劣,生产力低下,乡村民众经济匮乏,缺医少药,经常受到各种灾难的袭击,甚至某种并不严重的疾病也会危及他们的生命,并且时常有匪患骚扰。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一些原本赤贫的朝鲜族民众很难在一地安家立足,不得不频繁地流动。如民乐乡的红光、新乐、民安三个朝鲜族村落的多数人家都有数次搬迁的历史。民安村一位姓元的村民讲述,其4岁时随父母由朝鲜平安北道来到黑龙江五常地区,记忆中十年之内竟搬了九次家。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生活的贫困无着加上居无定所,使得朝鲜族民众渴望得到救助,驱邪避祸、祛病祈福的心理格外强烈。历史上,朝鲜半岛便具有信仰多种宗教的民间传统,如萨满教、天道教、基督教、儒教、佛教等等。迁移中国之后,在生存危机引发的精神恐慌之下,朝鲜族民众固有的宗教意识发生了种种变化,并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以各种形式甚至是十分激越的形式显现出来。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族村屯中,人们在信仰种种传统的朝鲜半岛本土宗教的同时,多神信仰也开始流行。人们不仅崇敬鬼、神、仙、佛,对人、神之间的沟通者——男觋女巫的信奉也十分虔诚。而如前所述的生存背景、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则是这些民间宗教信仰生成与发展的温床。在贫困与疾病的挣扎中,朝鲜族女性民众往往较之男性承受着更多的生活压力,她们需要从民间信仰中寻求心灵的抚慰,并且也只能以这种方式作为协调生活压力与心理平衡的手段。朝鲜族女性民众在民间信仰上表现出的狂热与盲从,与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需求无法满足有关,更与她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所形成的渴望救助的心理分不开。可见,中国东北朝鲜族的民间信仰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下生成发展起来的,我们只有拂去社会历史与民族生存史的风尘,才能客观而科学地审视中国东北朝鲜族民间信仰的种种特征及其变迁的动因。二、东北朝鲜族民间信仰的主要表现形态东北朝鲜族的民间信仰具有明显的现世功利倾向,讲求实用的特征非常突出。种种民间信仰控制着朝鲜族民众的心理与行为抉择,支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当日常生活中出现一些事件及变故时,这些信仰的功能与作用更是凸现出来,外化为种种信仰行为。在一些朝鲜族村落的调查中,笔者重点访问了一些65岁以上的老年民众,了解他们的信仰状况以及亲身体验,同时也通过他们了解一个世纪以来的民间信仰及其变迁状况。总体来看,东北地区朝鲜族的民间信仰主要表现为以下内容:1.亡灵信仰朝鲜族民众对亡灵的信仰具有传统性,人们普遍相信人死之后灵魂可以不灭,其灵魂仍然可徘徊于地狱和天堂之间。不过,多数调查对象都不情愿承认自己的亲人死后变成了鬼。但是,在人们深层的信仰意识中,人死即变为鬼,祖先也是不能例外的。在朝鲜本土的信仰传统中,祖先崇拜是重要的构成。当然,只有亡灵的观念在人的头脑中形成之后,才会出现对祖宗的崇拜。在朝鲜族传统观念中,家族中的成年人正常死亡后,便可以进入祖先的行列享受祭祀了。民间俗信亡者有“三灵”,一灵寓于“神主”(即亡者灵牌)奉于宗庙,一灵随尸体羁留墓穴,另一灵才赴阴曹地府。一些民众认为,亡灵是无影无形的,但具有超凡的能力。它们能变化形态或依凭于人,施人以祸福。因而,朝鲜族民众对于即便是自己亲人的亡灵,往往也怀有敬畏相加的复杂心理,既希望其佑福于自己,又害怕其作祟于己。在信仰行为上,则表现为对亲人的亡灵关怀备至,每逢一定节期,必向祖先灵牌行祝祷之礼,或于墓前插佛陀,祭献供品,以崇拜供奉的方式来安抚徼福(图1)。对亡灵的信仰,在朝鲜族丧葬习俗中多有体现。辽宁省宽甸县宝山村的朝鲜族老人亡故后,丧礼中有为死者“招魂”的仪式,即由死者的长子或巫师拿着死者生前的衣服,站在院中,围着供桌转三圈,边走边甩动衣服,叫着死者的名字,高喊“侍者把他好好带走吧”!然后把衣服扔到房顶上,再将死者全身所有关节处用12道绳索一一捆绑。绳索是用布条搓成的,特别强调要以反劲搓制。从这一仪式可以看出,人们在内心里是希望亡灵平安上路后永不返家的。围着供桌转圈,是使亡灵找不到归路;用反劲搓绳捆绑亡者全身关节,是唯恐亡灵挣脱绳索,诈尸作祟。总之,无论祖先的亡灵还是旁门外鬼,都使人们感到恐惧。在调查中发现,多数民众对这一信仰并不回避,对这一话题,他们谈及的尽是本人亲历的情景以及亲友、邻里的遭遇,皆为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事例,带有极大的蛊惑性和感染力。这里列举几例有代表性的个案:个案1 辽宁旺清门镇旺鲜村一位村民讲述:我的娘家婶儿在沈阳市于洪区农村住。60年代初闹自然灾害时饿死了。婶儿在世时和我家来往密切,她死后,我家总出事,儿子在外面喝醉了酒打架的这类事不断。我们村有个80多岁姓安的妇女,是巫师,我就请她占卜。安说:“你家总出事是你死去的婶儿闹的,她是饿死的,想吃饭。”于是我家按照巫师吩咐,用铁锅盖摆上三碟咸盐(朝鲜族有用咸盐打煞之俗,笔者注)和三碗饭,放在院中,祭奠完我婶儿,把饭也倒掉了。家中也渐渐太平了。(讲述人,朝鲜族,女性,1931年生)个案2 黑龙江五常地区民乐乡民安村一村民讲述:咱民安村前些年闹了一次鬼。村里有个年轻媳妇和家人吵架,一时想不开,就到村子北头的铁道上卧轨自杀了。此后,村子靠近铁道的那趟街开始闹鬼了。先是有户人家晚上只有女人在家时,门自己就开了,就见卧轨的小媳妇进屋来了,把这家的女人吓坏了。等丈夫回来了,她一说,丈夫不相信有这事。第二天晚上,她丈夫故意一人留在家中,结果死去的那个媳妇又进门来了,把这家的男人也吓坏了。其后,这条街上家家都受到了骚扰。村里有个老头不信邪,晚上到铁道旁巡视,结果遇上“鬼挡墙”(指人被鬼迷惑之后,往哪里走都好像有墙挡路,笔者注),转了一夜也未转出去。天亮时一看,老头这一夜一直未离开那个小媳妇卧轨的地点。村里人心惶惶,后来,只好请来巫师驱鬼,从此才渐渐太平了。(讲述者,朝鲜族,女性,1926年生)个案3 黑龙江五常地区民乐乡新乐村一村民讲述:我娘家在吉林省舒兰县镇郊乡。在娘家住时,村里有个年轻媳妇暴病而死,这家男人又娶了一个媳妇。新媳妇过门后,前妻扔下的一个孩子昼夜啼哭,新媳妇也常有病。这家人觉得有邪气侵宅,就请来一个女的巫师驱邪。巫师降神后,说是死去前妻的鬼魂在闹宅,家里才不安宁。还说鬼魂闹宅是在索要自己生前用过的衣物用品。这家人不知冤鬼究竟要哪些东西,就请巫师指点。于是鬼灵就附于巫师所持的法器之上,法器抖动起来,自己移动,一一指点出死者留下的鞋、袜、衣裤、簪子等衣物用品。最让众人吃惊的是,死者生前有一条毛线织的长围巾,新媳妇过门后,拆掉一半改织成短围巾,也被法器指点出来了。这户人家就将这些东西全都火化了,这家人从此平安无事了。(讲述者,朝鲜族,女性,1928年生)上述三例个案中的亡者均非寿终正寝:A饿死,B含冤自尽,C壮年暴病而亡。在朝鲜族民众的亡灵信仰中,通常将非正常而死的人称之为“横死鬼”,如冤死、饿死、吊死、难产死、淹死、夭折等等。这些亡灵一般都被民间视为凶鬼,认为最易作祟生事,是对生者构成威胁的最危险的因素。人们往往将生活中发生的死亡、疾病、灾难等归咎于这些恶灵鬼物的侵害,而人们对此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便是通过法事仪式来驱除这些鬼魅。2.巫觋信仰由于亡灵信仰在朝鲜族民众中传承久远,因而自古以来人们对各种驱鬼除厉的法术便笃信不疑,一些镇宅辟邪之神亦为世代的朝鲜族民众所奉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东北乡村,由于风气闭塞,民智晚开,加上长期的缺医少药,致使巫蛊势力弥漫全境。有资料记载,当时黑龙江等地“巫风盛行,家有病者,不知医药之事,辄招巫入室诵经。装束如方士状,以鼓随之,应声跳舞,云病由某祟,飞镜驱之,向病身按摩数次遂愈。或延喇嘛治之,亦大同小异”。(胡朴安,1986:84)对于人地两生的朝鲜族移民来说,经济匮乏与疾病威胁是人们生存的难点。易于染病且又无力就医,人们只能将康复的希望寄托于超自然的神力,拜托那些自诩能与神鬼沟通的人,帮助自己消灾除厄。由于某些巫觋也掌握一些粗浅的医疗方法,因而时有灵验之举,于是巫觋的神秘性、灵验性也在民间进一步滋蔓开来,形成十分深广的信仰。在对中国东北朝鲜族乡村巫觋活动的调查中发现,各地巫觋降神驱鬼的行术之法大体相似,主要为以下几个程序:摆供:主家在炕上摆一矮桌,桌上供有一铜碗大米,米里插有一把铜匙,匙柄套有一轴白线。桌上供有酒具,斟满米酒。桌上还立有3~5尺黄色麻布卷成的布卷。供品后面是神牌,由巫觋本人从家带来。有的巫觋还要在桌子上方拉一长绳,上挂纸幅,纸上书有事先写好的各路神灵之名。引鬼:主家敲起鼓或铜锣、铜盆,巫觋诵经引鬼。先命病者以草棍十数根占出奇、偶数,巫觋据此数字或掐指计算或查翻卦书搜寻是何方鬼魂前来作祟。然后命主家取出事先制作的圆形小糕饼数枚(富裕人家以大米面制,贫穷人家以玉米面制),将饼的两面沾上黄豆面,放在猪圈、牛圈、仓库等处,置饼之处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巫觋言说此为鬼魂出没所经之路,置糕饼意在引鬼。
 Copyright ©2022 广州田至鹤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保留所有权利
Copyright ©2022 广州田至鹤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保留所有权利
服务热线:13926267057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历德雅舍 网址:www.688zgdy.com
网站备案/许可证号:粤ICP备12076813号 技术支持:现科网络